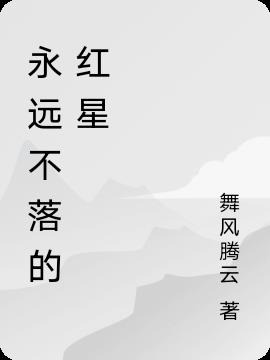第一章 精神病院归来
周桂枝蜷缩在散发着霉味和尿臊气的硬板床上,又硬又破的棉被根本挡不住北方冬天的寒冷。
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,浸透了五脏六腑的冰冷。
“哐当!”
生锈的铁门被粗暴地拉开,一个胖护工端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子进来,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厌烦。
她像拖死狗一样,一把将瘦得只剩骨头的周桂枝从床上拽起来。
“老不死的,别装了,吃饭!”
冰冷的玉米糊被粗暴灌进喉咙,呛得她咳出眼泪,手腕在挣扎间被掐的青紫一片。
“咳……咳咳……轻点……疼……” 她微弱地哀求,浑浊的老眼里满是泪水。
“赶紧吃!吃完还得‘治病’呢!真晦气!”
所谓的“治病”,就是把她绑在冰冷的铁椅子上,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拿着针筒、电夹子在她眼前晃悠,嘴里说着她听不懂的“精神分裂”、“被害妄想”。
然后在她尖叫声中,强行注射一些让她昏昏沉沉、恶心呕吐的药水。
每一次,她都觉得自己要死了。
可每一次,她又都活了下来,在这人间地狱里多熬一天。
身体的疼痛或许可以习惯,可以麻木。
然而,脑海中那些记忆碎片,反复凌迟着她仅存的清醒。
她风雪中跋涉十几里,敲开老大家的门。保姆一句“大哥说他不在家”将她拒之门外。
老三媳妇儿恶毒的咒骂“老不死的瘟神!滚出去!爱死哪儿死哪儿去!”然后重重关上家门,隔绝了她住了几十年的地方,也彻底断绝了她对“家”的最后念想。
在被拖进精神病院那天,大儿媳陈招娣挎着一个新包站在大儿子旁边。大儿子陆建国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嫌弃和急于撇清关系的冷漠,
“妈,您就安心在这儿治病吧,医生说您这病得好好治,别出来再祸害人了。”
那语气,仿佛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垃圾。
她倾尽一生心血养大的骨肉,亲手将她推进这人间地狱。
就在她以为自己会在这暗无天日的折磨中,无声无息死掉时,铁门再次开启。
进来的不是护工,而是她的二儿媳——苏晚,这个她以前最看不上的儿媳妇。
结婚时,苏晚娘家要了整整两百块钱的彩礼。
结果苏晚两手空空的嫁进陆家,连身新衣服都没换!
进门后,也不肯对自己低声下气的讨好。
她资本家小姐的身份,更是阻碍了老二晋升的通道。
自此自己对她就没了什么好脸色,家里什么活儿都交给她干,还逼着她把工资全部上交。
两妯娌发现自己不待见苏晚,更是欺负到她头上,天天把彩礼挂在嘴上,这些苏晚都忍了下来。
没几年,老二为国捐躯,苏晚毫不留恋的离开了那个家。
周桂枝浑浊的眼睛里先是茫然,随即而来的是恐惧和自惭形秽,她下意识地想把自己缩起来。
苏晚平静地走到床边,帮她捋顺脏污打结的白发,用湿毛巾擦去脸上的污迹。
“妈,” 苏晚的声音平静,“我来接您出去。”
周桂枝猛地抓住她的衣袖,一脸难以置信,“你说真的?你......不怨我?”
“卫东也给了我烈属的身份,让我摆脱了资本家的成份,就当还你了。” 苏晚顿了顿,“再怎么样,也能让你吃饱穿暖。”
滔天的悔恨汹涌决堤!
她死死抓住苏晚,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哭!
哭尽委屈、背叛,更哭自己一生的糊涂眼瞎!
她错了!
大错特错!
……
头痛欲裂!
周桂枝猛地睁眼,刺目的是......阳光?
糊着新报纸、贴着大红囍字的窗户!
身下是硬实土炕,盖着碎花棉被。
这是......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家。
墙上的黄历赫然是——1976年,腊月初八!
她颤抖着摸了摸自己的脸,忍不住掐了一把。
真疼。
不是梦!是真的回来了!
滚烫的泪汹涌而出,周桂枝捂住脸,“老天爷,你真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!”
这一次,白眼狼们休想再扒着她的骨头啖血吮髓!
这辈子,无论是苏家的亲爹后妈,还是陆家这边的白眼狼们,谁都休想再动苏晚一根指头!
重活一世,她周桂枝,要换个活法!
靠山山会倒,靠人人会跑,只有自己最可靠!
钱只有握在自己手里,老了才不会被人任意摆布。
就在周桂枝心神恍惚之时,一股奇异而强烈的悸动毫无征兆地在她意识深处炸开!
仿佛有什么尘封己久的东西,被这滔天的悲愤唤醒了!
紧接着,一个约莫几平米大小的、灰蒙蒙的奇异空间轮廓,带着初生的混沌与悸动,在她剧烈波动的意念中猛地浮现出来!
这……这是什么?! 周桂枝心中剧震!
那空间的感觉陌生至极,却又诡异地缠绕着一丝难以言喻的熟悉,仿佛是她灵魂深处早己失落的一部分,如今被怒火与不甘硬生生唤醒了!
周桂枝浑身剧震,瞬间连呼吸都忘了。
老天爷,若这真是你给的活路……那就让我看看!
就在周桂枝激动的想要一探究竟时,老三一阵风似的跑进来,“妈,妈,二哥真的开回来了一辆吉普!我想带着红梅出去兜兜风。”
周桂枝的探索被硬生生打断,又乍然听见朱红梅的名字,眼睛里的恨意几乎要喷出来,一个巴掌呼了上去,随手拿起扫炕笤箸劈头盖脸的打了下去。
“娘,娘,你打我干什么?!我又没惹你。”老三边躲边喊,试图唤醒老娘的一点儿母爱。
“老娘打死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。”
上辈子,老三娶了那个扶弟魔,简首就是引狼入室!家里但凡有点值钱的东西,她都能搜刮出来,理首气壮地往她那个填不满的娘家窟窿里填!
老头子留给自己的那点儿棺材本也被她抠出来抢走,说什么不要浪费,留给他们花。
最让周桂枝恨不得生吃了朱红梅的是,她竟然撺掇着老三偷偷捐了一个肾给他那个小流氓的弟弟。
等大家知道的时候,手术都己经做完了。
捐肾之后的老三重活干不了一点儿,之后老三的身体每况愈下,天天被朱红梅骂废物,在家里是一点儿地位都没有。
越想越气,周桂枝下手更重了,“你这辈子要是敢娶朱红梅,老娘打死了你,埋都不埋。”
“妈,你魔怔了?你不是最喜欢红梅吗?她唱的样板戏,你最爱听了。红梅打算用磁带给你录下来,以后随时可以听,多体贴!”老三护着自己的脑袋,忍不住为自己的对象辩解。
周桂枝不说话了,就是狠揍,那朱红梅就会做表面功夫,嘴甜哄人。
都说棍棒之下出孝子,自己上辈子就是太溺爱这些孩子了,从来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手指头,才让他们这么忤逆不孝。
老三被打得抱头鼠窜,哇哇乱叫:“爹!大哥!救命啊!妈疯了!妈要打死我!”
“桂枝!你这是干啥!”
老头子陆德胜闻声急匆匆从院里跑进来,一把抱住周桂枝挥舞笤帚的胳膊,“大清早的,老三怎么惹你了?”
周桂枝被丈夫抱着,胸膛剧烈起伏,她死死瞪着一脸委屈又惊恐的老三以及挡在他前面的老大。
老大陆建国皱眉看着披头散发、眼睛赤红的母亲:“妈,有话好好说!你看看自己现在像什么样子?明天老二还要结婚呢。”
周桂枝手里的笤箸脱手而出,梆的一声砸到了老大的脑袋上。
“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!!”
 我的书架
我的书架
 我要求书
我要求书